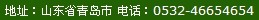|
﹀ —?01?— 前阵子,我突然没有任何事情就去了一趟庆云南街和干槐树街。 我走了一大圈,在庆云南街时,分别在成都日报社、二医院那里停下来看了看。就只是看了看。然后让自己回忆了一下当年的街貌,也不太想得起来了。医院门口的那几家面店和小饭馆已经没有了,而早年的成都晚报社,也就是现在的成都日报社,大门也不在庆云南街上了,开到前面的红星路去了。庆云南街是红星路的背街,当年,成都晚报社的地址是“庆云南街19号”。 然后我走到干槐树街10号。两个身着臃肿冬衣的男人在街沿的小桌子上摆开象棋,捉对厮杀,然后一堆同样身着臃肿冬衣的男人围观。这个景象是我熟悉的。我还想得起来当年那些围观男人们背在后面的手,有拿着一袋馒头的,有捏着一把葱的。 在门口犹豫了一下,还是走了进去。跟门口的景象一样,10号里面还是老样子,谈不上是一个院子,黑乎乎的一排自行车棚和老宿舍之间,是一条挺窄的通道,几棵长在隔壁第三幼儿园的腊梅树,枝条伸了过来,在车棚上支着,想必每年隆冬这里还是会飘荡几缕腊梅花香。 △|年初冬的干槐树街10号的老院子 —?02?— 有好些年,我住在干槐树10号,然后走5分钟的路,到庆云南街19号上班。 干槐树街非常小,就如《成都城坊古迹考》中所记载的,仅长95米。现在它还是这么一条短短的小街。在成都市第三幼儿园的隔壁,就是干槐树街10号,四川日报宿舍。这是川报分散在成都市区好些处的宿舍区的一个,规模很小,就一栋六楼的房子。先生李中茂供职于四川日报,我们当年住在最后一个单元的左手二楼。那时,我的家也很小。建筑面积70平米左右,老房子,除了小小的厨房和卫生间,有两间房,没有客厅,只有过厅。房间开间倒也不小,我们把其中的一间房设置为客厅兼书房。 在宿舍门口的对面,是一条小巷。但人家不叫巷,叫爵版街。爵版街连接干槐树街和藩库街。当年,整条爵版街就是一个菜市场,这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。这个菜市场的核心地带不在巷头,也不在巷尾,而在巷子的中间,那里有一个肉摊,摊主每天细细地在案板上剁着肉馅,同时也剁着一些细细的姜末。可以买上两块钱的肉馅,摊主用菜刀挑上一坨,放进塑料袋,往杆秤上一搁,准得很,就两块钱左右,前后差不了一毛,然后摊主再用菜刀尖挑上一撮姜末放在肉末上,系上塑料袋递给顾客。没一句话。他知道顾客是用这肉末做圆子汤的。而肉摊旁边的菜摊,总是有豆芽菜在卖,都是些肥白的黄豆芽。黄豆芽旁边是稍显寒酸瘦削的绿豆芽。买了黄豆芽就不会再买绿豆芽了。黄豆芽入汤,绿豆芽清炒,一般都是这样的家常做法。 这回走到干槐树街,自然就走了一趟爵版街。菜市场没有了,只有街边的便民超市和几家蔬果店。跟记忆相比,这条小巷宽敞了不少,骑自行车的少年从我身边飞驰而过。 △|菜市场被取缔了的空荡荡的爵版街 —?03?— 经常有人会说起职业生涯这个词。一般来说,我正面应对这个词汇的时候很少。作为一个职业作家,我已经居家写作十来年了。对于一个不上班的人来说,写作这个职业是存在的事实,但因为没有职场,所以很难与职业生涯这个词找对契合的点。 要说我的职业生涯,相对来说理直气壮的,就是在庆云南街19号的十年。我在成都晚报前后供职差不多就是十年。 正式的回忆本身很难对我有所触动,能够触动我的东西往往是猝不及防的。庆云南街的十年,我总是匆匆忙忙地出入着,现在回想那时的自己,似乎只能看到一个瘦削的人影,想不起来在忙些什么。我在很多年里都是一个相当瘦削的女人。离开报社之后,父亲给了我几本工整仔细的剪贴本,那里面,有“本报记者陈洁”刊载在成都晚报上的所有报道,从第一篇几十字的简讯开始。我不知道有多少曾经当过记者的人有这么齐全的个人新闻作品资料?现在这几本剪贴本还在我的书柜里,是我的宝物。父亲沉默寡言,吝于表达,从小到大,我几乎没有听过父亲对我的当面夸奖,但我知道,他一直以他的方式ios开发总监北京市中科医院好不好
|
当前位置: 庆云县 >映话突然走到庆云南街和干槐树街
时间:2018/2/2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经济庆云159吨啤酒出口蒙古国,为德
- 下一篇文章: 民生关注便民资讯1月30日2月6日南岸
- 热点内容
-
- 没有热点文章
- 推荐文章
-
- 没有推荐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