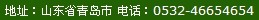|
(老照片难寻,文中少量图片均来自网络) 我的故乡是盐山县庆云镇。年的冬天,我出生在那个人口不足人的小村庄——中秦村。而中秦到庆云镇的直线距离不足3公里。 28年前,是我第一次长时间地离开小村,离开庆云,到盐山县城东关中学读初中,再加上盐山中学的三年高中,一共6年。那时,跟同县的别人介绍自己时,说我是庆云的。后来到四川读大学,再介绍自己时,说我是河北的。都是河北人时,则说我是沧州的。待到大学毕业回到沧州市工作,又成了我是盐山的。若恰好碰到一个对盐山格外熟悉的问,盐山哪儿的?就又成了我是庆云的。兜兜转转近30年,原来我还是庆云的! 只是,现在介绍庆云时,往往还要多加一句:是河北庆云,不是山东庆云,河北庆云是镇,山东庆云是县。其实,山东庆云的历史,又岂是能与我河北庆云相比的? 最初对庆云产生特殊感受的一刻,缘于小时候有一年春节,看到父亲在堂屋里供奉先人的族谱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两句话:原籍山西洪洞县,移迁来到庆云城。自此,庆云城作为承接我的祖先的生存之地,在我的生命里,便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。 城里 儿时,我们习惯把“庆云”称为“城里”。现在想来,“城里”这个叫法应是源自庆云曾是历史上的老县城的缘故。 城里,顾名思义,肯定是区别于村里的。那时,去城里,最寻常,也最正当的目的就是“赶集”。庆云集是逢阴历的三(初三、十三、二十三,下同),五,八,十都是集,也就是每十天有四个集。这与周边集市每十天里只有两个集形成鲜明对比,也充分彰显了庆云历史上作为商贸流通重镇的特殊地位。每次逢城里是集的那天,山东庆云,阳信,无棣,乐陵,河北盐山,海兴等方圆几十里的多个县、市的人蜂拥而至,自早晨太阳露头,逐渐把城里纵横的几条街道挤得水泄不通,人群一直蜿蜒到城南紧邻着的漳卫新河高高的河堤上。而收市往往也跟季节和日头有关,冬季的午后人流便开始分散,但夏季,往往到太阳西下还有人流连。 在我的记忆里,每次去城里赶集仿佛都是一件大事,特别是跟母亲一起去的时候。早早起床,换上新衣服,梳洗打扮得整整齐齐,格外精神。或许,在母亲看来,去城里赶集是一件非常郑重的事情。就如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里说的,你无趣是因为缺乏仪式感。母亲这份不自觉的庄重确实让我有一种强烈的仪式感,而且有一种小兴奋——跟着母亲去赶集,小零食,水果自然是少不了的。这对一个才几岁的小家伙来说,是多大的诱惑和向往啊!而如果哪次去赶集时母亲不去,只是父亲带着我,母亲总是要特意嘱咐父亲:记着给孩子买点吃的,别跟着你白去一趟。父亲不大会挑那些本就没有多少花样的零食,记得最多的是他会在回来的路上,在出了城里的西关北边,路东有个国营的包子铺,给我买几个包子,看我吃得很香,他就会笑得很欣慰。 城里的集,按那个年代所交流物资的内容,用途,分为多个“专业市场”。记得比较清楚的有粮食市、牲口市、鞭炮市。 跟着祖父去的多的地方是粮食市和牲口市。那时,祖父往往赶着马车或牛车,到了市外把牲口拴在某棵树上,或者让我坐在车上,或者牵着我的小手到市里面这儿看看,那儿转转。在粮食市里,有时候会卖掉一点高粱或者黄豆,回去时再带着点小米或者黏玉米粒儿等。而到了牲口市,我就常常躲在祖父身后,那些身形高大强壮的牛马驴骡,在我看来就是庞然大物,让人望而生畏。我喜欢那些洁白温顺的小羊羔,或者偎依在羊妈妈身边,或者在母亲的肚子下面调皮得钻来钻去。就算我怯怯地伸出手去摸摸它们柔软的毛,它们也只是扭下身子,甚至会伸出粉色的小舌头舔舔我的手背。只是,牲口市里那混合着草料,粪便,牲口的喘息的奇怪的气味,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异常清晰,虽然很多年都不曾再闻过。 鞭炮市是每到春节前才有的,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,进入最兴盛的阶段。那些卖鞭炮的摊主,往往举了长长的竹竿,把一挂挂鞭炮挂在顶端点燃,互相比着赛着放,看谁家的鞭炮声更响,更亮,便能吸引来更多买主。鞭炮市收市后,地下就积了厚厚的一层碎纸屑。有些小孩子在里面捡没有燃着的独头鞭,再点着的那声响,便格外清脆响亮。因为害怕鞭炮的声音和电光,父亲去买鞭炮时常把我放在城里的姑婆家。姑婆是祖父的同胞姐姐,嫁到了城里。我们去赶集,有时候就在姑婆家吃饭。 在城里集上最后的清晰记忆,是年上大学前夕父母为我置办行装,买了那把两折叠的小花伞。那时,买大件东西或者高档点的服装鞋帽就已经有了门市,商店,而不是儿时的露天市场了。 医院 医院,于我是格外重要的一个场所——我和妹妹都是在那里出生的。 还记得30医院,位于庆云城北。沿城里老十字街口北行约米左转路西,有一条不宽但平整的水泥路,不足医院。医院不是现在这种开放式的大楼,而是围墙围着的一片四方院,带着明显的时代特征。大门宽敞豁亮,显得朴素而大气。院里的小道好像是铺着青砖,路两侧种有整齐的白杨和梧桐,路面干净,院里安静。几排清医院的全部了,门诊、病房虽然陈旧但整洁,简单的几个科室也算比较齐全。和蔼可亲的大夫们穿着白大褂,偶尔有戴着厚厚的瓶底儿的,便显得格外斯文和有学问。 母亲生我的时候是难产,那时患有妊娠高血压的她抽搐得没有了意识和知觉。大夫见孩子迟迟生不下来,遂决定给母亲实施剖宫产。30多年前的隆冬清晨,医院里没有暖气,大夫让在产房里生起火炉以便增温。就在把母亲推上手术台的那一刻,我却艰难地落了地。父亲说,刚出生的我,头被吸钳吸得变了形,长长的,特别丑。但是,因着我之前父母已经夭折了一个男孩(我那未曾谋面的医院出生,但是甫一落地便已没了生命体征),这次母女平安,他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 四年后的夏天,医院里,顺利生下了妹妹。她生下来就比我胖,也比我壮实。生小妹的当年,医院,我开明通达的父母,积极响应国家号召,父亲带着母亲做了绝育手术。 从出生一直到小学毕业,我的身体都不是很好,感冒发烧,吃药打针是家常便饭。医院里的大夫跟父亲和我都成了老熟人。平时的头疼脑热去乡卫生所拿点药,吃几天便见效了,但顽固点的毛病,或者乡卫生所看不医院。 8岁那年春节刚过,祖母去世,这对我是个很无法接受的意外打击。也是在那年,出水痘,换牙,我本就孱弱的身体出了些格外的问题。一颗本来已经松动但长歪了的乳牙被新长出的两颗门牙挤得变了形,怎么也掉不下来,加上感冒发烧,引发了牙齿炎症,睡了一宿觉,第二天嘴里竟然吐出一个血疙瘩。后来没办法,父医院拔牙。 我胆子不小,也够坚强,打针吃药从来不哭不闹,这点让父母很省心。但看到大夫桌上摆放的那些冰冷坚硬,毫无感情的器械,长长的针管,还是吓得发抖。我战战兢兢地问:阿姨,是要给我在牙上打麻药吗?记得那个温柔和蔼的女大夫说:小姑娘,不打针,咱们把麻药喷在牙周围就好。我在她善意的谎言里放松下来,直到被注射麻药的针头刺痛反应过来时,那颗细长的异形牙齿已经被拔下扔在了旁边的托盘里。我用哀怨忧伤的目光看着她,泪水在眼里打转,但始终没有落下来。父亲及时地把我搂在怀里,跟我说笑分散了我的注意力。 其实,拔牙真的不痛,痛的只是那一下针扎。就如我们在多年以后回忆往事,背景和过程已经模糊,清晰的只是其中的某个时点,某个细节。(待续) 赞赏 长按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偏方方法海口治疗白癜风医院
|
当前位置: 庆云县 >原创庆云,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具象一
时间:2017/11/11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下周三11月1日,山大第二医院心脏超
- 下一篇文章: 庆云知味坊平安中秋幸福月活动
- 热点内容
-
- 没有热点文章
- 推荐文章
-
- 没有推荐文章